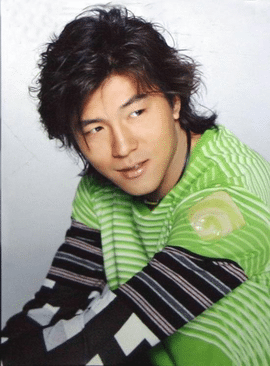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由边疆异族建立的满清王朝,以小制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几十万八旗奴役驱使几万万汉人,竟统治中国两百余年。

满清帝国既以强大的征服者的姿态,拥有暴力统治的基础,又根据中国传统皇权,驯服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这种背景之下,满清时代的文化活动,毋宁也是在皇权的掌握之下。康、雍、乾三代,朝廷发起的文化活动,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阳明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明末清初,中国读书人发展出了自由心态,并且对过去的历史展开检讨,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和顾炎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凡此,满清政权都不愿发生;王船山《读通鉴论》中提到的反清的民族主义,和吕留良等人主张的复明运动,更是受到强力的排斥和压制。
满清皇室一方面以修《明史》的名义,抓住对明清递换之际的历史解释权,取缔民间修撰的明史稿,发动大规模的文字狱,吓阻汉人再做同样的尝试;另一方面,政府主动编撰大型的丛书,例如《四库全书》,以这个方式选择性地排斥不利于“夷狄”的记载。这些大型的编撰工作,发动了大量学术精英参与,借此将这些儒生笼络于政府掌握之下。乾、嘉以后朴学大兴,儒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证和校勘上,致力使经典回归原来的面貌。
这一活动,在好的角度说,是排除后世对古代经典的扭曲和脱落之处;换一个角度来看,致力于还原经典的原貌成为学术主流,对于经典的阐释就无人再做努力。于是,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经典固定了,不断更新经典意义的活力也就丧失了。儒家经典只停留在朱学的解释,也就是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言,乃是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

经过清初百余年皇权的强力干预,中国的儒生都成为俯首从命的书智障者。明代留下的经世传统,只存在于颜元、李的实用之学中。汉代今文学派以下,对于宇宙论和历史发展论的解释,只是不绝如缕而已。儒家传统的结晶化——也就是僵化——持续到晚清,恰当中国面临文化危机的时候。在将近两百年之久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缺少开展的活力。
这一特色,可以见之于清代的艺术:例如清代绘画的主流几乎都是模仿过去的作品,山水画画家“四王”的作品缺乏创作性。又例如,清代的瓷器和家具,多姿多彩而繁琐,失去了明代青花瓷和明代简单线条的家具那种素雅的艺术风格。在主流以外的艺术圈,例如“扬州八怪”等人,却发展了一些新鲜的主题和风格。
在文学和表演艺术层面,满清时代的成就乃是小说和京剧,两者都是主流以外的边缘人物创造的成就。文学领域里,民间说书人为小说提供素材,而且由此创作了一些长篇著作。曹雪芹当然不是民间的说书人,但是他也不属于当时文化界的主流。现在成为中国传统舞台艺术重要形态的京剧,乃是一批徽班演员撷取了昆曲、汉剧等地方戏曲的精华,综合为复杂而优美的舞台艺术。凡此例证都指向,政治力量的高压与收买固然驯服了文化的精英群,那些边缘地带的人物却还是可以在夹缝中脱颖而出,对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既然已经僵化,于是,一些民间的宗教活动从边缘出发,掌握了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最值得注意者,乃是根据中亚传来启示性信仰发展而来的白莲教。这一个教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民间道教、佛教和摩尼教。在元代末年,最大的一支抗元武力就是明教的教徒。
在明代,明教潜伏在民间,逐渐转化成为白莲教。乾、嘉时代,白莲教的活动从川楚到山东、山西都有分布,范围广大,活动频繁。乾、嘉之际,白莲教甚至曾经一度攻入紫禁城,在各处的起事也是前仆后继,成为当时主要的内乱之一。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回教,既有西域族群反抗满清的成分,也有伊斯兰教教派起事的性质。满清中期以后,频繁的回乱,从甘肃到云南,延续颇久,也给政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规模最大的一个宗教性的活动,则是咸丰时代的太平天国。
这一个冒充基督教的民间运动,实际上也是民间教派的活动,而且加上了反清复汉的族群意识。到清代快终了时,义和团的活动则将族群意识的矛头转向于反对西方力量,它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仍旧属于中国民间教派活动的传统一脉。这几次大规模的变乱,可说是因为主流文化的儒家留下了一片空白,无法满足一般平民的精神需求,才由民间的教派活动填补了空缺。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国,有一批中国的学者,例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愿意和西方来的学者对话;又如,方以智更是从西方文化的启示上发展出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
在满清时代,西方的影响却逐渐淡化。胸襟最开阔的康熙,自己也从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但是,也是康熙,为了大礼的争议,实质上停止了西方的传教活动。这些西方教士从此只能在钦天监工作,因为相较于中国传统天文学和中东传来的阿拉伯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毕竟更为精确。政府限制教士们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动,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来往。
甚至于在武备方面,满清也采取保守态度,不再使用和发展西方的火器。如上章所述,在满清入关前后,明、清交战双方都曾使用火器。替满清做前锋的汉军部队一路征战,使用铳炮,势如破竹。在康、雍、乾三代,向北方和西方扩张时,满清的军队使用过大量的火器,其中很多是开国时汉军部队留下的武备。几次大战役,这些火器几乎消耗净尽了。
在乾隆时代,进攻大、小金川,满清军队已不见重装备,全靠火枪作战。然而,乾隆认为满州武勇是以骑射为长,不应该数典忘祖,放下自己的传统。清早期的三代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制造和修理火器的兵工厂。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才重新接上发展火器的传统。清初十七、十八世纪时,民族国家在西方逐渐兴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发展武备为要件。十七世纪初期的枪炮,和当时中国使用的火器,精密程度相差不远。
到了十八世纪初,中国没有再发展,而欧洲的军火技术却已经突飞猛进。单以火枪而论,从点火线的“铳”,已经发展成用撞针敲击子弹发射的步枪。如同前章所叙述,乾隆时代,访问中国的英国代表团回国时曾报告:中国是个没有国防军备的国家。果然,在鸦片战争时,广州虎门炮台上只有平定三藩之乱时使用的“红衣大炮”,对方的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海军炮!

自从蒙古打通了东西之间的海陆信道,欧亚大陆上知识的传播相当流畅。中国的许多传统工艺,例如瓷器的烧釉、毛丝织品的混纺技术,甚至于传统中药的药材,都有相当多的改变。康、雍、乾三代以后,中国的工艺基本上停滞不动。明末,西洋“水法”传入中国,水压喷泉和流水技术也被用来作为庭园和灌溉的设施。八国联军时烧毁的圆明园,其建筑的方式,包括格局和上述水法,都有西方的影响。清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建筑技术不再容纳西方的方法和观念。
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到了清末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都已经湮没不彰。不仅文化闭关,实际上所谓“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整个清代,除了皇室宫殿、庭园以外,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规模巨大的工程,主要的只有防止黄河泛滥的河工和保持漕运畅通的运河工程。
中国传统上的筑路、开河、国防工程等大型的公共建设都未见进行。明末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海船制造技术,自从满清接收中国台湾以后,中国再也不能制造远洋的大船,其技术也停滞下来。凡此现象,都显示了,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张和发展—这也许真的是结束的开始。
经济方面,一般人也称康、雍、乾为“盛世”。若以人口数字而论,明代本来已经有超过一亿半的人口,经过明末大乱,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满清开国时,人口大概只有八千万上下,经过休养生息,康熙时代大概又过了一亿。康熙对于自己统治中国的成就非常自满,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诏书:“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从秦、汉开始,中国列朝国家的收入,一部分是人口税,一部分是田亩税,有时再加上丝帛,作为农余生产的产品。经过康熙“永不加赋”的诏书,政府收入从此只有田赋为主,再加上特种税“榷”和过路税“关”。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单单以既有的田亩作为税基,其实是不够用的。
从好的方面看,政府不收人口税,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加快。换个角度看,自古以来,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由于人口的增长不再是政府关心的项目,官民之间也就失去了互相联系的脉络。汉代“社”和“里”的管理乃是国家机器直达到基层的体制。当官民之间不再有联系时,政府能够与民间相接触的点,也就局限于地方官和地方绅士;一般老百姓必须要经过公、私两条管道,才能够理解到“国家”的存在。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

当然,人丁不再列入国家统计项目时,人口大幅增加,已有的生产资本—土地,就会不足以维持大众的生计。增添的人口,必须要有新的土地资源来养活。于是,满清增长的人口不断开发新的耕地。前面曾经说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与内地人口大量移入西南有直接的关系。
在内地,人口从窄乡移到宽乡,其实已是常见的现象,例如赣南、皖南、湘南,这三片在南岭北麓的丘陵地带,不断吸纳黄、淮流域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人口。明末,四川的人口大量减少,所谓“湖广填四川”,就指大量移民从湖北东部、南部入川。满清将今天的东北各省视为老家,不许一般人移入,然而,山东的人口其实经常渡过渤海,进入辽河流域,再由此扩张到今天东北的全部。
这些内部的人口迁移,在明代已经开始。不过明代的移民是官家主导的,而清代这种内部的迁徙,却是百姓自发的。从清代的官书资料中,常见地方官忽然发现有成万的外来人口移入该地,于是慌忙上奏,甚至建议清剿。其实,这种忽然出现的大量新人,就是自动移到该地开荒的窄乡人口。
在这一个现象下,增加的人口成为开拓田亩的生力军。田亩开拓了,地方当局可以从新开的田亩上征收田赋,这是“歪打正着”的现象:“盛世滋丁”替国家增加了征收田赋的耕地面积,因此,国家也有相当稳定成长的新税源。整体而言,国家的经济体虽然在质的方面并没有改变,在量的方面确实扩大了。到了嘉、道时期,中国人口大约过了二亿,到清末时,就到四亿左右了。由于人口增长而经济体扩大,乃是满清时代中国经济的特色。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中国出口的项目,仍旧是以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向东南亚一带输出的工艺品。欧洲国家经过长程贸易,将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产品。中国吸纳了大量的白银,应当是非常富足,然而,这些经过贸易顺差而获得的财富,并没有转换成再投资的资本,反而造成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
对于丝织品和瓷器生产地的东南地带,确实有累积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也只是支撑了富人奢侈的日常生活。北方和内地的一般老百姓,反而要承受通货膨胀、购买力不足之苦。英国发现,对华贸易经常入超,力求找到可以平衡逆差的商品。他们终于发现可以用鸦片贸易来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从此开始,鸦片毒品输入中国的数字年年上涨,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此消失,不仅农村开始凋敝,而且因为吸毒,中国人的健康也大受影响。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圈,而自满清中叶开始,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却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满清的统治机构,如前面所说,是满汉两套重叠的官僚系统,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效率。也如前所说,那些经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学习的是僵化的经典,畏惧的是不测的君威。他们习惯于唯唯诺诺,不做积极的抗议,只是顺从意旨,以保富贵。当然也有些能干的官吏,可是在大潮流之下,少数优秀的官员难以发生作用。
从乾隆时代开始,当国用不足时,政府往往以捐纳作为筹款的手段,捐纳的报酬可能是虚衔,也可能是实质的官职。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政府的正常税收完全不足以应付国用,捐官的收入成了政府筹款的常态。政府之内充满用钱财买官得到职位的人员,这样的政府机器,不可能有正常操作,更不要说具有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清末内忧外患,正是必须要因应新的情势、做重大改革的时候,可是,满清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精英,都已不能担起扭转局势的任务。

综合而言,满清二百多年来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来虽然一样是征服王朝,满清疆域扩张到极限,几乎超过了汉、唐最盛的时代,两百年人口增加的幅度也是史无前例。凡此所作所为,似乎满清比蒙元高明。实际言之,蒙元的高压统治只是一味地使用武力,并没有机会严重地伤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蒙元时代还保留一些独自运作的能力。
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那二百多年,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开展的阶段,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经过两百年来的伤,再也不能有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
中国在皇权体制下,结合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精耕细作的农业、市场经济,有过两千年之久的不断调节、不断成长的过程,成为世界主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