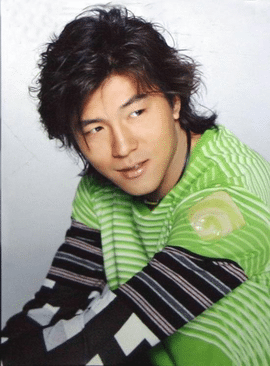徽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作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黄河流域,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从贾人数众多、活动区域范围广、经营行业众多,在中国商界称雄三百余年。然而,这股曾创造辉煌的商业势力,为何在清朝中后期走向衰落了呢?

萌芽成长
三国时,吴国雄据江东,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已呈繁荣趋势。东晋建都建业,中原资财大半随之南迁,经济活动中心由北移南。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着江、浙、皖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地就已成商贾集中之地。这些地区环绕徽州,商贸活动带动徽州与毗邻地区的物资交流,东晋时的徽州商人就这样乘势而起,萌芽成长。
唐时,徽州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茶的运销遍布国中,甚至漂洋过海,运抵国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就包括祁门西南乡。唐咸通三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说,徽州“山多而田少”,山区“植茗,高下无遗土”山民“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税,悉恃此。”但凡茶叶上市,“贾客咸集,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繒素求市,将货他乡者,摩肩接踵而至。”
徽墨、歙砚,堪称徽州二绝。徽墨首创于唐末奚超父子,南唐后主李煜盛赞徽墨,敕封奚超父子“墨务官”,并赐姓为李。徽州每年须贡龙凤墨千斤。歙砚取材于婺源龙尾山,故名龙尾砚。苏轼有《龙尾砚歌》赞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五代时,绩溪所产的龙须纸,质地洁白光滑,也可谓徽州名产。南唐后主李煜将其收藏于澄心堂书殿,故名“澄心堂纸”。据《砚谱》云。李煜所收藏的徽墨、歙砚和澄心堂纸,“三者为天下之冠。”
这些文化产品,不仅为权贵们所收藏,也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市场需求颇大,获利颇丰。徽州商人能不整装结篋,负之远销。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这里虽也是个市镇,可作为京都不免有些狭陋。历代王朝无不追崇皇家气派。赵构初迁临安便大兴土木,筑宫建殿,仅御花园就有四十余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宋的官吏们跟着效仿,一个个在西子湖畔构楼架阁,以资眺览,制船造舫,纵情游玩。
一时间,杭州城里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西子湖畔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建宫筑殿离不了竹木漆原材料,而徽州又盛产这些原材料。徽州人将这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达杭州,于是,便使竹木和漆的运销利市三倍。杭州又为“闵商岭贾”的集结之区,徽州商人把土产售与闵粤商人,再把闵粤物产转运内地。稍一周转,富商大贾应然而生。如此暴富暴起,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经商。唐宋时,徽商已不像东晋时那般稚嫩孱弱,而已如破土春笋,茁壮成长。

雄飞商界
明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颁令改变盐法,把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给予换取食盐,准其在指定区域贩销的制度,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自由贩卖的制度。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向为盐商集聚中心,晋、陕商人人地生疏,难以与徽商竞争。徽商由此乘隙而入,改以经营食盐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由此,经营盐业成为徽商的重头戏,五行八作也缘此而蓬勃兴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开设墨庄、茶庄。书商开设书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贩卖棉布、丝绸、米谷、纸张、瓷器等,还有的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贩卖珠玑、香菜等。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大到国外,明代嘉靖年间,徽商许栏、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罗及东南亚各国有生意往来,他们的商业活动竟远及葡萄牙。总之,什么可以赚钱,何处可以牟利,徽商无不经营,无不涉足。
徽商由小本经营暴富后,或数人共营,或一家独营,开设钱庄和典当,获取暴利。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及江北,”在河南者达“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县志》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徽商有上贾、中贾和小贾之分。百万为上,二三十万为中,余皆属下。盐商资本雄厚,多以千万计,稍次也是数百万。
徽商并非全以贩运为主,也兼营一些生产活动。如郑天锁、朱之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染纸厂,运转于苏浙鄂豫冀鲁等省。江长公在房村制造曲蘖,销售范围由“徐邳以达京师”。他们雇了很多佣工,其生产规模已具有手工工场的形式,融工商活动于一体。徽州人大多以经商为职业,在商人的比例中大约为十分之七,极盛时甚至超过。明万历年间,徽商汪克在河南所开当铺竟达213家。徽商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北至幽燕、辽东,西至滇、黔等,东南至海外,可谓“贾人几遍天下”了。
明清时期,徽州富接江南。一些文人为生计所迫,趋之若鹜,麇集徽州。徽商为附庸风雅,将这些文人揽为食客。钱能通神。徽商还以钱财宝货结纳权贵。墨商罗小华就曾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而成为其入幕之宾。他们还和官府勾结,挪欠朝廷巨款,富商吴养海大言不逊地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二十余万。
徽商经商有道,获得高额的商业利润,也就必然以课税、捐输等各种形式奉纳给朝廷。如康熙十五年至嘉庆九年的一百三十多年,两淮盐商捐银三千九百多万两,米近二万二千石,谷近三十三万石,上述捐输多为徽商承担。此外,徽商还向朝廷捐奉军需银二千二百多万两。

无徽不成镇
自明代中后期始,经商在淮扬的徽州人也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开始在这里融资兴业。明代王世贞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把资金的十分之九投入于侨寓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扬等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丰厚的财富基础之上。
明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侵掠扬州,近二百家盐商惨遭抢劫和焚毁。知府借盐商三万两银,于旧城外增建新城。新城建成后,民居鳞次栉比。清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说:“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羸,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到了明万历年间,扬州的盐商多达数百家,资本总额超过三千万两,说“扬州富甲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淮安地处南北要冲,是漕运、盐务和榷关重地。徽商迁居于此,他们大大改观了淮安的面貌,以致使这里渐次成为“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仪征是淮南盐运的中枢。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指出:“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盐业贸易的发展极大的刺激了市镇化的建设,清代前期的仪征“路接竹西,津通扬子,鹾客辐辏,估客骈阗,俗尚繁华,由来日矣。”清代袁枚曾有诗夸耀仪征的繁华胜景:“渡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簇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
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徽商将它看成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淮盐引岸地跨六、七个省,行盐口岸大半在湖广,而汉口就是淮盐转运口岸的最大中枢。盐商和运丁等聚居于此,在当时汉口的百种行业中,做淮盐生意的当为大宗。
早在康熙初年,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和新安巷。到了雍正十一年,又扩建新安巷,“置买房店,扩充径路,石镌‘新安街’额,开辟新码头,兼建‘奎星楼’,为汉镇巨观。……更收买附近会馆房屋基地,造屋数十栋以为同乡往来居止,并设经学,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旅邸肄业之所。”作为徽商聚居地的汉口就这样成为繁华热闹的市区。
凡是徽商聚居之地,哪怕是滨海荒陬,哪怕是乡村僻野,只要他们麇集骈至,只要有盐场署所在,那里就能形成集市,那里的经济就会发展,文化就会振兴,那里就会成为“烟火万家,商贾辐辏”的市镇。

夸富斗奢
自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以来,这种重农轻商,等级贵贱的排序,几千年来几乎没变。巨商大贾尽管富可敌国,可仍然排在第四。这种价值取向的阴影一直在徽商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而这又成为反作用力,刺激徽商要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自我,彰显自尊,以补偿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方式就是一掷千金,铺张扬厉,有文献是这样记载徽商的奢靡之风:
“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同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加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
徽商为附庸风雅,征召名优,开设戏馆。于是,扬州也就成了昆曲的第二故乡。清顺治、康熙、乾隆皇帝都是戏迷,每次南巡经过扬州必征歌逐宴,欣赏昆曲。徽商也由此培养了自己对戏曲的兴趣,纷纷招苏州名优名角,办起了私家戏班子,以致使苏州、扬州成为全国戏曲的中心城市,有所谓“苏班名戏淮扬聚”“老昆小旦尽东吴”之说。
徽商不仅舍得在昆曲戏班子上大把花钱,也不惜钱财,构筑园林,以博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康熙、乾隆的南巡更召来徽商营造园林之热,大量新奇的园林拔地而起。时人记载盐商张氏园林,可见徽商营造的园林之一斑:
“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夏则冰琑竹簟,冬则锦幙貂帷,书画鼎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为贵;古玩无真赝,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吏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金钗十二,环侍一堂,赏花钓鱼,弹琴度曲,唯老翁所命,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眉目清扬,语言便捷,衣以色别,食以钟来。……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亦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四壁玻璃射之。”
夸富斗奢的风气给徽商后人产生了极不好的作用,有诗证之:“年少儿郎性格柔,生来轻薄爱风流。不思祖业多艰苦,混酒银钱几时休。”先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在这些年轻一代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只是一味的追求享乐和挥霍,这也是徽商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向衰落
徽商的兴盛,纯以两淮食盐的运销为恃。徽商的衰落,尤以淮盐运销办法的改变而改变。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纲运制即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行票盐法即政府于盐场设局课税,无论任何人,只要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盐政新法改行六年之间,不仅消除了盐商的亏欠朝廷的数千万两银票,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千万计。
这笔巨款是盐商于正常利润外,官商勾结,共同舞弊的结果。陶澍改革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因为它直接危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动摇了徽商淮盐运销的垄断权。仅以扬州为例,徽州盐商夸富逞胜,争奇斗巧,建起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序》载,盐政新法后的清道光九年,徽商多“歇业贫散”“看管园丁不能糊其口,就曳折木瓦变卖”。经过四十多年的耗损,“昔日繁华胜地,变成废墟。”
太平天国时,徽州是太平军的活动中心,当然也就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频仍战事,兵连祸结。徽商深受其扰,先是地主武装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亲自督师祁门,明火执仗,纵兵大掠,徽州府被洗劫一空。清军在徽州烧、杀、掳、掠,使富丽的徽州尸横遍野,庐舍为墟。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备受摧残,大伤元气。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使徽商遇到了强劲的敌手。徽商在省外各地经营的钱庄,敌不过外国商人的银行。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廉物美,方便耐用,也渐次取代徽商手工生产的产品。如布匹、纸张等,连仅此一家的毛笔、徽墨、歙砚等,也几让钢笔挤出了市场。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的快,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或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由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只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洋商的活跃,洋货的倾销,使徽商不堪一击,当年的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淡出商业舞台。

徽商从萌芽到衰落,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悠悠岁月。在如此漫长的的日子里,他们一代一代地担囊负橐,背井离乡,登山涉水,备尝艰辛,以争锱铢之利。徽商虽然成为了历史,然而,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篇章。他们聪明勇敢,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