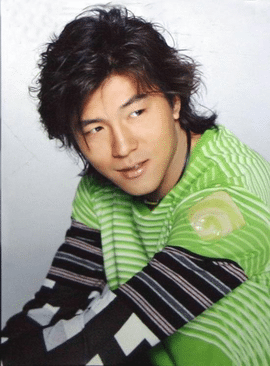刘牢之是东晋时期名将,生长于尚武世家,其人面色紫赤,须目都异于常人,性格深沉刚毅,为人足智多谋。刘牢之一生大起大落,迅速达到人生巅峰,转眼间又跌入谷底。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东晋北府将领刘牢之的生平,用“举一反三”这个成语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这里不是用的成语本意,而是说的刘牢之一生中最重要的四件事:一举成名和三次反叛。其中真正让刘牢之传名后世的,是让他饱受诟病的三次反叛。这三次反叛,让刘牢之大起大落,迅速达到人生巅峰,转眼间又跌入谷底。自己将已经得到的一手好牌打烂,不但丢了性命,而且还背上了“倒戈将军”的标签,常常被拿来与吕布相提并论,可以说是身败名裂。
刘牢之出身将门,世代以勇武知名。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建武将军谢玄镇守广陵防御前秦,大量招募劲勇,刘牢之因为骁勇得以应选入军。谢玄用刘牢之为参军,率领一部精锐士兵为前锋,打仗百战百胜。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北府兵,东晋赖以对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一支劲旅。刘牢之凭借率领北府兵在太元初年与前秦作战的战功,迅速升迁为鹰扬将军、广陵相,人生起步相当顺利。
太元八年,前秦大举进攻东晋,淝水之战爆发。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五千赶赴洛涧,迎击前秦梁成的两万前锋部队。在梁成已经凭据涧水险阻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刘牢之率军径直渡水攻击,大破敌军并阵斩主将梁成,随即分兵阻断对方退逃的渡口。败逃的敌军争渡淮水,刘牢之乘势掩击,杀获万余人,缴获敌军所有器械物资。
这一仗极具传奇色彩,是以五千对两万,以一敌四,而且对方还占据险要,竟然大获全胜,可见刘牢之和他率领的北府兵战斗力之强悍。此战虽然只是淝水之战的前锋战,却极大提升了晋军的士气和信心。后来淝水主战场前秦军队稍微一退便兵败如山倒,恐怕便有受这一仗影响而心态发生变化的原因,刘牢之则因此一举成名。

刘牢之第一次反叛是反王恭。王恭出自名门望族太原王氏,是晋孝武帝的大舅子。谢玄死后,孝武帝用王恭掌北府兵,镇守京口以为朝廷屏藩。王恭此人性情刚直,对看不惯的事常常当面正色批评,丝毫不给面子,得罪了不少人,包括会稽王司马道子。晋安帝即位后,司马道子执掌朝政,与同为太原王氏的王国宝等人弄权。王恭对此十分不满,双方闹得水火不容进而互相图谋。
隆安元年,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势力,起用此前因与后燕作战不利而被免官的刘牢之,起兵清君侧,迫使司马道子诛杀王国宝等人。隆安二年,因为对司马道子任用司马尚之以及割豫州四郡归江州等不满,王恭以全军委与刘牢之,再次起兵逼宫朝廷。而这次刘牢之被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策反,临阵倒戈,导致王恭败死。
事后朝廷兑现承诺,刘牢之如约取代王恭,接管兖、青、冀、幽、并、徐、扬七州及晋陵的军务,从一名只是带领偏师作战的将领,一跃成为手握重兵的强藩,获得了实质性的重大利益。当然临阵倒戈这事干得很不厚道,刘牢之同时被谴责背主求荣也不算冤,但也不是没有自我辩解或自我安慰的余地。
一是王恭毕竟是以下抗上,理上有点站不住脚。刘牢之反叛王恭还可以说成是选择拥护朝廷的大义,舍弃忠于王恭的小义。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逼迫朝廷,这样的事不可多为。而王恭干了一次还来第二次,画风似乎也有点不对,在朝廷和其他地方势力看来,已经颇有跋扈的味道。晋室南渡以来,地方势力威胁朝廷的事屡屡发生,有王敦、苏峻、桓温反叛在前,王恭手握重兵,一言不合就对朝廷武力相逼,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效仿?何况王恭第二次起兵本就过于任性,是被庾楷利用了,除了殷仲堪、桓玄等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支持者并不多。刘牢之也劝过王恭,但王恭不听。
二是王恭性情倨傲,不善抚御下属。王恭门第高贵,虽然倚重刘牢之的作战能力,但只当作行阵武将对待,视之为走卒,并不太礼遇,刘牢之自然心中不忿。王恭第一次逼宫时,起用王廞为吴国内史,令其起兵响应。然而事成之后便马上要求王廞解职,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王廞不服,起兵反抗王恭。刘牢之被王恭派去击灭王廞,只怕也会感到有些心寒。
鉴于这两点,刘牢之反叛王恭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当时对刘牢之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恐怕更大程度上是对刘牢之掌握北府兵感到眼红。荆州方面的杨佺期、桓玄就打着为王恭申辩的旗号,起兵进逼京城建康,威胁朝廷要求除掉刘牢之。刘牢之也不客气,率北府兵进驻建康附近的新亭,迫使对方退兵,而刘牢之则得以牢牢掌握北府。随后率军平定卢循孙恩起义,风头一时无两。单纯从成败的角度来看,刘牢之反王恭这笔买卖还是划得来的,决策不算失误。

刘牢之第二次反叛是反司马元显。元兴元年,桓玄起兵叛乱,沿长江顺流而下直逼建康。朝廷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领江州刺史,率军讨伐桓玄。此前一直表现勇猛的刘牢之突然变得畏首畏尾起来,担心打不过桓玄,又担心打胜以后功高震主而被掌权的司马元显猜忌。桓玄派人一劝,刘牢之居然不顾刘裕以及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等人的极力劝阻,轻易就向桓玄投降,让桓玄轻松攻入建康,导致司马元显及其父司马道子被杀。
这次反叛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让人难以理解。刘牢之以建军元老的资历掌握北府兵,坐镇战略要地京口,挟平定孙恩卢循起义的胜利之威,可谓名声大振。以此时的地位和实力,桓玄多半不敢轻举妄动,而朝廷也没有能力说拿下就拿下,真不知刘牢之的恐惧从何而来。
刘牢之完全可以从道义或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从容做出决策,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其实这应该算刘牢之的绝佳机会,如果当时选择打起拥护朝廷的旗帜率军平叛,毫无疑问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实力。要是有点野心,那以后恐怕就没有刘裕什么事了;没有野心的话,则可以效仿陶侃,自保也不成问题。
就算刘牢之不帮朝廷对付桓玄,那么也可以坐山观虎斗静观其变,突然毫无来由地向桓玄拱手投降,直接就跪了,表现得何其怯懦。与其担心打败桓玄以后不为司马元显所容,倒不如担心桓玄过河拆桥。从倒戈王恭之后朝廷并未食言来看,至少司马元显有过说到做到的经历,可信任度总还是比狡诈的桓玄要强。事实上桓玄攻入建康诛杀司马元显后便立即翻脸,第一件事就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意图夺其兵权。刘牢之这次反叛让自己身负背叛恶名,不但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惹祸上身,真是枉作小人。

刘牢之第三次反叛是反桓玄。这次反叛与第二次反叛前后相继,严格来说,只是停留在策划阶段,并没有真正实施。桓玄动手收夺刘牢之兵权,刘牢之这才如梦初醒,找刘裕商量,想要到广陵与女婿高雅之会合,打起匡扶社稷的旗号讨伐桓玄。刘裕认为此前坐拥强兵数万却望风投降,已导致威望和人情尽失,而桓玄则因此名震天下,此消彼长,已无可与抗,拉着何无忌自行返回京口。
刘牢之随后召集部属商议,参军刘袭当着众人的面指责刘牢之一人而三反,人品太差,不能自立,与众多佐吏当场散去。刘牢之信心崩溃,后来又见刘敬宣去京口搬取家人没有如期返回,以为已被刘袭所杀,绝望之下自杀。
刘裕和刘袭的话可谓五味杂陈,既有惋惜,又有鄙视,还有掩盖不住的愤怒,并且流露出对刘牢之怯懦表现的极度失望。部属纷纷抛弃刘牢之,并非是因为刘牢之反复无常而不可信,而是认为刘牢之太过无能,继续跟随刘牢之,不但没有前途,还会跟着取祸。这完全是从利益角度出发,并不是从道义角度考虑。
刘牢之此时的状况确实非常被动,但也不至于到了刘裕说的大势已去的地步,刘裕夸大其辞,恐怕也是为自己的离去找个合适的理由。刘袭等人既然打定主意抛弃刘牢之,直接明说跟着你干没有出路,也有见利忘义的嫌疑,而指责刘牢之不忠诚当然就是极好的借口。就像现在要跳槽,如果老板为人厚道,多少还会有些愧疚;但要是老板本就刻薄抠门,弃之而去自然不会被人指责,自己也不会有心理负担。
即便是刘袭等人离开后,也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从刘牢之自杀后将吏还收葬其遗体归丧丹徒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力量。以北府兵的战斗力,奋起一搏,未必便输。然而刘牢之最终居然选择自杀,心态已脆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说之前拱手投降堪比曹魏末年高平陵政变时面对司马懿讹诈的曹爽,此时自杀则堪比东汉末年拱手让出冀州后面对袁绍恐吓的韩馥。回想刘牢之当年率领北府兵在洛涧临险冲击前秦军队的勇气和胆略,简直怀疑这是不是同一个人。

第一次反王恭,刘牢之赌赢了,单车变摩托迅速上位,拿到了一手好牌。第二次反司马元显则完全是昏招,一张牌打错,局势瞬间反转。第三次虽有反叛的想法,自己却没有信心把这局牌打下去了,最终自暴自弃。刘牢之的失败,关键在于第二次反叛的决策失误造成局势逆转,导致失去了众人的支持。
而众人抛弃刘牢之,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刘牢之多次反叛,而是认为刘牢之怯懦而不能成事,不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是众人趋利避害的现实选择。换句话说,刘牢之不是败在人品,而是败在能力。只是刚好人品上出现了反复无常的硬伤,又与传统的道德观相违背,于是替能力上的不足背了锅。至于刘牢之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怯懦,大好局面下突然脑袋短路,可能与其深受门第等级观念影响形成的的自卑心态有关。
自东汉以来,门阀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到东晋时期已经登峰造极,门第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高门面对低门有着理所当然的心理优势,鄙视是存在于骨子里的。像太原王氏这样的高门,甚至连陈郡谢氏这样的大族都看不起,认为是新出门户。龙亢桓氏也算士族,在代表人物桓温权倾一时的情况下,太原王氏的王述仍蔑称其为“兵”,拒绝嫁女到桓家。即使经过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断打压,门第等级观念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视,到唐代时唐文宗都还忿忿不平,自家两百年天子,门第居然还不如崔卢。
刘牢之虽不是寒族,但最多也就算低级士族,何况还出身历来被士族看不起的将门,在鄙视链中只能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即使打仗再厉害,掌权的高门大姓也只是毫不客气加以利用而已,能给予多少尊重是谈不上的,王恭的态度就足以证明。总之,连贵为皇室都得屈服于门第等级观念的环境下,刘牢之他无力摆脱思维定势,面对高门大姓自觉气短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甚至怀疑刘牢之反叛王恭属于一时冲动,是受到王恭慢待积累的怨气,加上朝廷许以的重利,两方面因素合力造成的非理性行为。若是当时头脑冷静,只怕慑于太原王氏的名望,未必便敢倒戈。而后来面对桓玄,既没有长期的积怨,也没有重利的诱惑,有的就只有骨子里对高门大姓的畏惧,选择投降也就好理解一点了。
与刘牢之相比,刘裕则是彻彻底底从最底层起步,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而能够不拿门第等级当回事。没有刘牢之的心理阴影和思想顾虑,刘裕敢于向士族阶层发起挑战,聚集北府兵残余力量,毫无悬念地打败已然徒有虚名的士族阶层,取而代之也就是必然的了。而刘牢之不能突破这一层障碍,则连自保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改变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