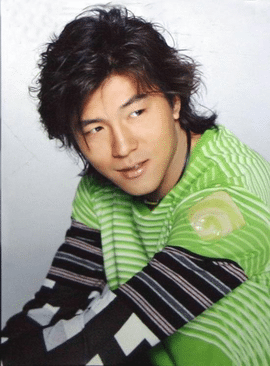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西汉中叶,官场上出了不少的可人,排第一的,当属张敞。张敞留名后世,在于一份参奏,说他身为朝廷命官,在家里给妻子画眉,不成体统。汉宣帝虽说是个明白人,听了这话,却也当回事了。不过,他没像昏君一样,稀里糊涂就把人扔进监狱,而是找本主儿来核实一下。张敞来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臣闻闺房之内,夫妻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意思是说,如果给妻子画眉就要治罪,那么,在床上干事该怎么办呢?一句话点醒了汉宣帝,他没事了。但画眉的美名,或者说在某些道学家看来是臭名,传了下来。
丈夫给妻子画眉,怎么会有罪过呢?其实,这事如果放在汉初,根本就没有人会提出来。女人化妆描眉,出来招摇,人人都挺乐呵。男女之间,哪怕不是夫妻,秀秀恩爱,没啥大不了。但是,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开始还马马虎虎,慢慢越做越像,儒生们讲究的礼教,开始被人们当回事了。当然,女人的自由度也开始降低,地位自然也跟着降低。所以,画眉这点事,也就可以拿来嚼舌头了。被告了御状的张敞,其实也是儒生。《汉书》上讲,他是习经之人,但却偏要画眉。以他的性格,被告之后,多半还会继续画。风流如斯的张敞,其实是个能吏。一辈子做的官不大,最大不过是京兆尹。首都的地方长官,官阶不低,但麻烦事不少。京城嘛,满城高官厚爵之人,一不留神,就碰了哪个得罪不起的。
但是这个麻烦官儿,其实是他自找的。有一阵儿,胶东一带贼盗蜂起。地方官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偏偏张敞没事找事,自请到胶东为官,皇帝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马上任命他为胶东相——胶东王的相国——相当于胶东地区首席地方官,还赏了他黄金三十斤。张敞去了之后,就用这赏金开出赏格,盗贼抓了其他盗贼送官,不仅免责,而且有赏。一时间,盗贼互相,不其他人的也怀疑同伙要对自己下手,于是群盗解体。张敞以贼制贼,初见成效。
然而,长安城的治安,就大有问题了。大街杀人的强盗倒是不多,但街市上的小偷乌泱乌泱的,成群结队,害得百姓和官员都叫苦不迭。大大有名、官声最佳的黄霸,由颍川太守任上调任京兆尹。黄是讲礼义教化的,苦口婆心,干了几个月,治不了这些毛贼,铩羽而归。于是,京兆尹的担子,就给了张敞。
张敞到任之后,经过一番的调查,发现这些毛贼是有组织的。每个片区,都有一个贼头。由于毛贼的多年供养,这些贼头现在都跟体面人一样,居华屋,出有车,童仆成群,还有自己的产业。于是,张敞就把这些贼头都找来,把他们都委任为京兆之吏,让他们负责治贼。贼头们做了“官”,大开宴席,毛贼们都来送礼庆贺,觉得这下子有靠山了。酒酣耳热之际,贼头们趁着毛贼酒醉,一一在他们的背上做好记号。这些毛贼出门之后,凡是背上有记号的,悉数被拿下,一天就拿了几百人。再由拿下之人追查过去,没几天,长安城大体太平了。以贼制贼之策,再建奇勋。
有功的张敞,没有升官,在京兆尹的任上一干就是九年。京兆尹这个买卖,谁都干不好。张敞出了名的会做官,即使是这样,还是得罪了人,最后因好友杨恽的牵连,好些大官都弹劾他,他却不识相地上书营救朋友。所以,道上传他就要被罢官了。正在这时,他指派门下吏絮舜去办件事,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不办,说是张敞就要被罢官了,总共不过五日的官运了(五日京兆),能奈我何?张敞知道后,马上将这个絮舜抓起来,严令属下昼夜究治,竟治其死罪,而且马上处死。
当时的地方官,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可以独立判人死刑,开刀问斩。当然,如果案卷有瑕疵,则可能被御史弹劾。唯一的禁忌,是春天不能行刑。怕的是处死人上干天和,导致灾异。其时,冬日已尽,马马虎虎算是春天了。张敞抓紧时间,在立春前夕杀了这个蔑视他的家伙。杀之前,张敞还遣人告诉絮舜:“怎么样,我这五日京兆,杀不了你吗?”此事上达皇帝,原本汉宣帝还犹豫要不要办他,这下非办不可了。于是,张敞成了平头百姓。
张敞成为平头百姓之后,长安的治安又开始不好了。一日,皇帝派使者到张敞家,说是皇帝有旨,要张敞跟他们走。家里人吓得要死,说是皇帝要杀他了。唯独张敞不害怕,笑着说,“我已经成了老百姓,若要杀我,派个郡吏来就办了。皇帝派使者来,肯定是他要用我了”。进宫见皇帝,果然,汉宣帝是要启用他。
启用他不是为了长安的治安,而是更大的事——冀州出了大股的贼寇。不是偷鸡摸狗,也不是拦路打劫,而是有扯旗造反之嫌。见了皇帝,张敞第一件事是为自己辩白,说“我杀的那个家伙,一向受我的厚爱,突然之间觉得我只能做五日京兆,就撂挑子不干了,这样背恩忘义的人不杀,简直没天理”。皇帝正在用人之际,只好听张敞抱怨完,然后任命他做冀州刺史,让他去救火。到了冀州,张敞故技重施,通过关系,找来若干当地能够降服的亡命之徒,拜之为属吏。有了耳目,张敞而后打探到当地贼盗的魁首所在,一举拿下。其余的贼寇,都躲进了当地的广川王府,广川王和他的兄弟一直都在庇护这些人。张敞尽发郡国之兵,亲自带领,兵车百乘包围王府。然后顶着风险,张敞进王府搜查,
将所有贼寇一网打尽,当着广川王的面,就把这些人都杀了,头颅就挂在王府大门上。然后张敞还不依不饶,上书弹劾广川王。汉宣帝网开一面,没有把这王爷废了,只削减了他的封户。
京兆从来难治,哪个朝代都如此。京师之地,王公贵族多,达官贵人多,皇亲国戚也多。互相攀连,牵一发动全身,究治不法,弄不好就碰到了哪个大人物。加上京师繁华,市场繁荣,来往人员广且杂,是匪类藏匿和作恶的好去处。而这些匪类,也难保不跟大人物有勾连。所以,好些牛人在别的地方为官做得挺好,到了京兆,往往就栽了。西汉京兆尹做得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赵广汉,一个就是张敞。
赵广汉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皇帝的“忠狗”,一面严刑峻法,一面广布眼线,每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犯罪分子。赵广汉对权贵和权贵亲戚家人敢犯禁律者,也严惩不贷,决不宽假。甚至,这些人没有犯罪,仅仅因为皇帝不喜欢,他也会毫无顾忌地下手。霍光死后,赵广汉知道皇帝对霍光不满,就带人到霍家搜查,砸掉了霍家的买卖。
一般来说,无论赵广汉惹了多大的乱子,皇帝都不会治他的罪。顶多降一级官职,然后再给他恢复。但是,赵广汉这样的跋扈,惹事必定越来越多,招来的嫉恨也越来越重。终于,他做得太出格了,跟当朝宰相魏相迎面相撞。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赵广汉派人查抄了宰相的府邸。其时,汉宣帝还没有打算弃用魏相,赵广汉横过了头。就这样,赵广汉倒了霉,墙倒众人推,被判处了死刑。临刑,长安百姓都来替他讲情,要皇帝留着他,保一方的太平。可是,人还是身首异处了。
张敞治理地方,其实跟赵广汉差不多。无非是以贼制贼,以盗治盗。所谓的耳目眼线,原本就是匪类。所谓的治理,也无非是求个面上的太平。贼盗,是不可能真的清理干净的。但大面上的秩序肯定会有,不至于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每个大点的案子,张敞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还要破案,基本上都能破得了。大人物丢了贵重的东西,跑了不想走失的童仆,要找都能找到。百姓因为没有了白昼行劫,也能有点安全感。
张敞的高明,在于不大得罪权贵,尤其不会为了皇帝去得罪权贵。只给皇帝看家护院,不给皇帝做“猎犬”,四处猎人。即使抓到了确有造反证据的广川王刘姬,也不去动他,把决定权留给皇帝。虽然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难免得罪人,但张敞开罪的人要比赵广汉少多了。班固说,张赵之间的差异,是张敞习经通春秋的结果。其实,张敞所为,还真不像个儒者,他习经,大概只是为了仕途(西汉中叶,皇帝已经很喜欢任用儒生了),本质上,他还是个法家,或者说,是一个巧宦。只是,他比赵广汉更知道节制,知道借力打力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后世的城市管理者无论何种面目,其实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