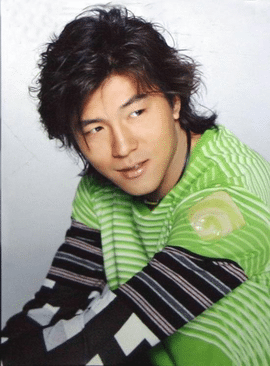朝鲜皇帝汲汲于皇族为自己辩护,在某些明代官员眼中,这是一种“矫情”,究竟是一种“矫情”还是另一种说法呢?当今许多学者认为,《大明会典》之所以被称为“宗系辩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鲜人以仁义、孝道为基础,捍卫了自己国家的王权。

然而,这个说法只停留在表层,其更深层次的理由和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我们有一种预感,在十六世纪,在朝鲜,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朝鲜皇帝不顾历史,支持“宗系辩诬”。
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十六世纪朝鲜《大明会典》的辩护中,到处都有朝鲜著名学者的影子,他们或活跃于北京、汉城等朝野,或活跃于士林、武林之中,对“宗系辩诬”的风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朝鲜立国之初,朱子学在佛教和勋旧派的压迫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儒家理论的发展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进步,但总体上还在宋儒所能了解的范畴之内。
在世宗王朝建立了各种文化体系之后,不管是在诠释经学还是在治国上,他们都变得越来越成熟,到了十五世纪后期,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旧体系进行强烈批评和攻击的新的知识分子集团。
成宗时代,由金宗直,金宏弼,金安国,金正国,赵光祖等人所组成的文人群体,在朝堂上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士林派以“至治主义”自居,主张君臣名分,极力抵制争权夺利,从而招致了崇古党与独裁君主的不满。
于是,在燕山皇帝统治时期,士林派遭遇了“戊午史祸”,因为士林派对太上皇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导致很多人被污蔑为叛国,不少人被杀,或者被贬。再加上燕山君掀起了“甲子士祸”,想要将王权彻底释放出来,对士林派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中宗反正”以后,金宏弼的门徒重新回到了官场上,并对当时的中土和各地实行了一种理想化的政策。其中,赵光祖在当时的官场上成了士林学派的领军人物,而金安国、金正国两兄妹则成了当时民间奉行“礼”的典型。
在这些人当中,赵光祖是朝鲜“道”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李滉、李珥等人公认的“道”的开创者。赵光祖对中宗的建议是“崇正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他认为士林应该作为治理与教育的主要对象,君王应该对他们加以爱护与信赖,将政事制度化地移交给他们,这样才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
赵光祖以其“道”的政见,给“儒生”的兴起带来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从而使得“儒生”在中宗末年得以形成,并在其后的朝鲜政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赵光祖与金安国两人的不懈努力,《朱子家礼》在民间广泛流传,“忠臣”“孝子”“烈女”的儒教道德思想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从而使儒教在中国得以“礼俗”的普及。
但是,因为对功名利禄的批驳,以及对王权的制约,士林不久便遭遇了“己卯士祸”,赵光祖被杀,许多士林首领或门人因此而被赶出了朝堂,而明宗时代的“乙巳士祸”更是把士林逼到了权利的边缘。
四大士灾看似对士林派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实际上,他们的兴起让他们感到了畏惧,而且,在经历了士灾之后,他们的儒家的观念和政治观念,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十六世纪下半期是士林派道文化形成的黄金时代,出现了李彦迪,曹植,金麟厚,李恒,奇大升,徐敬德,成浑,李滉,李珥等著名学者。特别是李滉、李珥这两个“顶峰”,对朝鲜四端七情说、人格性同说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产生了这两个学术流派。
李滉、李珥等人在十六世纪后期推动了韩国性学的体系化,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与实际政治相联系,形成了“流派”与“政党”的组合。
李珥死后,二教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形成了东人和西人两个派别,东人分为南人和北人,西人分为老论和少论,到了16世纪末期,也就是朝鲜的玄宗年间,就开始了党派之战。
从这一点来看,“宗系辩诬”能够在历代王朝中得以实行,并被推送至北京,其实质是因为当时的文人为了保持纯粹的王权而表达了自己的孝顺之意,文人在“宗系辩诬”中基本上占据了舆论引导与道义声音的支配地位。
当然,士林对于“宗系辩诬”的拥护,也遭到了“勋老派”的排斥,例如《己卯党禁录》所列的“文臣”,就有许多人在“文臣”、“文臣”、“文臣”等方面的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