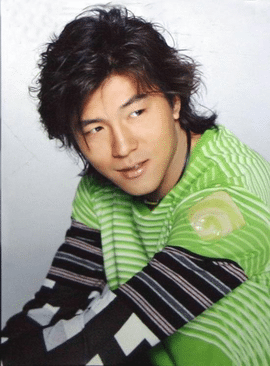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支持一种“未经限制的”享乐主义,由此说明美德对于实现幸福进而快乐的必要性,他在《高尔吉亚篇》中则反对以快乐最大化为核心的享乐主义,由此提出一种适应性的幸福主义。

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的相关观点
在其反对不自制的论辩中,快乐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是,因而人们有时应选择痛苦而不是快乐。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反对享乐主义的意见似是而非,因为这些反对者并没有想清楚享乐主义的真正蕴含。
这种属性上的统一意味着把善性还原为快乐性质,我们之所以把事物看作善的,是因为我们以为它们是快乐的,但我们把事物看作快乐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善的。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主张的享乐主义不是要替代幸福主义,而是要提出某种对善的论说,而幸福主义把这种善当作我们的终极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称之为享乐式幸福主义。
苏格拉底所支持的这种享乐式幸福主义还具有规范方面的蕴含,它意味着人们应当实现以快乐为目的的幸福。在苏格拉底看来,要实现这种幸福,其关键在于纠正我们由于短视而带来的各种误判,比如正如空间的接近性使我们认为眼前的事物要大于其实际之所是,时间的接近性也使我们夸大当前的快乐和痛苦。
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认为,我们需要“计量的技艺”来准确地算出由某个给定行为产生的快乐与痛苦总量,确保我们不会受到短视的误导。
他进而指出,公认的美德实际上是这种“计量的技艺”,并且由此可以说美德就是知识,因为美德之养成和践行,需要且应该基于这种计算苦乐的科学。反对享乐主义的流行意见认为,快乐是时好时坏的,因而可能出现不自制的情况。
苏格拉底的以上观点表明:这种不自制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问题在于信念方面出了错,我们一旦基于正确的知识(在此是计量科学)而形成健全的信念,就不会认为不自制是可能的,而总是会保持信念与行动的一致性。因此,苏格拉底似乎可以支持他在这一辩论开始时坚持的那个论点,即不自制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中的相关观点
在《高尔吉亚篇》关于享乐主义的论争中,苏格拉底的主要对手卡利克勒斯是一名享乐主义者。由对正义的辩护引出关于享乐主义与幸福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包括正义在内的美德对于幸福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足够的。卡利克勒斯对此反驳说,正义与幸福是冲突的。
我们是通过把快乐最大化来实现幸福的,且通过提高嗜好的强度和紧迫性来增益我们的快乐。因此,我们实现幸福的途径是,养成最大的可能嗜好并确保我们拥有满足这些嗜好的资源。
正义是一种关注他人的美德,要求我们正义地对待他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幸福而对其所需资源的追求,让我们有理由不正义地对待他人,因为满足欲求的资源是有限的。正义作为美德得不到辩护。
论点是卡利克勒斯所持有的享乐主义立场,可相容于《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的“未经限制的享乐主义”主张。论点是关于正义作为美德之性质的判断,它或许是古希腊通行的 观点,但正义是否有益于正义之人本身,这个问题虽与论点相关,在此却是未予明确的。
论点中蕴含着资源有限性这一小前提,它和可视为大前提的论点一起,可以导出论点表达的基本结论,即幸福的要求与正义的要求是冲突的。其中包含一个幸福主义预设,即幸福为至善之名,而美德作为善是有益于幸福的。因此,在卡利克勒斯看来,一种关于幸福的享乐主义观念蕴含着,我们有理由以牺牲正义的方式来满足这些欲求。
接下来看苏格拉底的回应。对于论点中资源有限性或稀缺的经验事实,苏格拉底并没有提出异议。如其早期对话中的假定所表明的,对于论点蕴含的幸福主义预设,苏格拉底不仅享有且其预设显然更强,但并不同意论点所显示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他不同意论点的看法。
对于论点中对正义之性质的判断,苏格拉底虽然承认正义在习俗的意义上是一种关注他人的美德,但同时认为正义在自然的意义上也关注自身,亦即自我对灵魂和身体的管理,并且无论是在习俗还是自然的意义上真正的正义都在于平等地分享。
苏格拉底的两种快乐观之比较
基于前两部分的梳理,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和《高尔吉亚篇》中对享乐主义分别持支持和反对的态度,但这两篇中的享乐主义是不同的,《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所反对的,并不是《普罗泰戈拉篇》中的一般意义的享乐主义,而只是以快乐最大化为核心的享乐主义。
通过对这两篇中相关主张的比较,苏格拉底在这两篇中对快乐的描述是一致的,都被描述为由欲求的满足而产生的心理状态,但对快乐的价值定位有明显的区别。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认为,快乐本身就是善,并且被解释为幸福的原因。
按照这种解释,快乐作为善不仅不受外部条件的影响,是一种内在的善,而且美德被解释为计量苦乐的技艺,在此意义上,快乐似乎还是一种终极善。但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虽然承认快乐是善的,但快乐不等同于幸福,更不是幸福的原因。
换句话说,快乐在此不被理解为终极善,它是否是内在善则存疑。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在这两篇中的相关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不一致。
如前所述,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的相关观点相容于卡利克勒斯的快乐最大化这一享乐主义前提,甚至可以说,前者支持或可能发展成后者。但是,苏格拉底对后者的批判态度表明,他无意让其快乐观往后者的方向发展。
《普罗泰戈拉篇》中的相关讨论针对的议题是不自制,亦即个人的行为选择是否存在与其信念不一致的情况。《高尔吉亚篇》的相关讨论是由正义议题引发的,并且卡利克勒斯的快乐最大化主张蕴含这样的理解前提,即苏格拉底谈论的正义是关注他人的习俗正义,与资源的社会分配相关,而卡利克勒斯主张的正义是一种以个人自利为核心的“自然正义”。
就苏格拉底针对不自制议题而提出的快乐定位而言,我们可以推想,他所设定的是一种理想条件下的个人价值选择。这里所谓理想条件,是指暂时搁置各种社会性的因素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上的冲突。或者说,苏格拉底所讨论的不自制这个议题是抽象掉各种社会因素而单就个人行为中信念与选择之间的关系而论的。
相比之下,习俗正义所设定的社会情境对快乐本身及其实现提出了各种限制性条件,因为快乐即使其本身是善的,在社会情境中也由于要获得满足欲求的资源而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冲突,比如说资源有限性带来的与他人的冲突、与其他价值之间发生的选择上的冲突、信息或知识不完备带来的冲突等。
因此,正如即使承认个人自由本身是善的,在社会情境中也必须为了他人自由或其他原因而予以限制。
苏格拉底快乐观在古希腊 学中的发展
作为柏拉图的同代人及苏格拉底的弟子,昔勒尼学派的创始人阿里斯提卜通过放弃苏格拉底的一些其他主张,提出了一种即时的享乐主义。根据阿忒纳乌斯的记载,阿里斯提卜乐于接受快乐的体验,且认为它是那个目的,而幸福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并且他说,它是仅仅一次性的。
像那些浪子一样,他认为,无论是对过去之满足的回忆还是对未来之满足的预期,都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他是单单通过当下一次性的快乐来辨识善。他把曾经享有的满足以及将要获得的满足看作对他毫无价值的,其根据是前者已经不再,而后者仍没有到来且是不清楚的———这正如那些自我放纵者的态度一样,他们认为唯有当前的才是对他们有益的。
由此可见,阿里斯提卜坚持了《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快乐观的基本观点,即快乐本身是好的,并作了改造或发展:其一,把快乐作为唯一且终极的目的,为此不惜放弃苏格拉底的幸福主义立场。其二,放弃苏格拉底所谓计量的技艺所蕴含的理性规划观念,转而诉诸感觉体验。
其中第二点实际上构成了昔勒尼学派的认识论基础,他们唯一信赖的是我们的感觉而对其他一切都抱有怀疑态度。按照这种观点,人生是片段式的、零散的而缺乏统一性,由此摧毁了幸福主义的认识论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批评阿里斯提卜的这种享乐主义观点,但不可否认,阿里斯提卜通过这样的改造让享乐主义更具有理论融贯性。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这种以否定人生统一性为认识根据的 观并不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
总结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快乐观虽然并非其 思想最核心的部分,但其快乐观的提出及其发展,却涉及其理论的各个核心部分,也对古希腊后来 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以考察其快乐观及其在古希腊的流变为线索,从一个侧面把握以苏格拉底为源头的古希腊 思想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