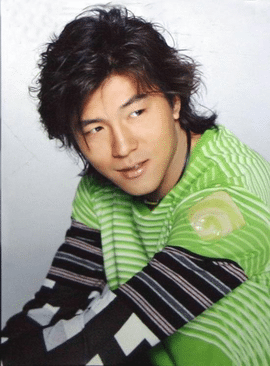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法感”是古埃及人民,尤其是他们的统治者对法的理解与看法的总和。追溯到埃及早期的文化,埃及人已经“摆脱了武力,摆脱了法制,摆脱了竞争,摆脱了协作”。
而在统治集团内,则出现了“以自己的自觉为核心,以自己的自觉为准则,来制订和执行法”的现象。所以,在埃及社会中,最先具备法制观念的是国王,僧侣团体,以及权贵们。

作为埃及至高无上的君王,他们的法制观念更多地表现为对自己统治阶层的保护。为保护自己的私利,六世派比一世曾经派出宰相乌尼去调查皇后篡夺皇位的事件,这一事件被记载在阿拜多斯的一座石碑上。
从奈菲里尔卡尔的诏书中可以看出,古代埃及君王对于神庙成员及其财物的保护是出于对神庙利益和神职人员的保护。
《教谕》中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僧侣为国家效力,否则一律送交审判。”为使其作为统治阶层的手段,即国家机构能够继续正常运作, 菲尔卡乌霍尔在《科普图斯诏》一书中,发布了一张上埃及各州的详细清单,各州下面还进一步细分出若干小型的行政区划,这些区划区划都是比较自给自足而没有自主权的。
因为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神职人员在埃及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主导地位。虽然牧师的律法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但在古代,牧师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却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代表他们的君王来侍奉上帝,所以,他们就像上面文奈菲里尔卡尔的旨意中所说的那样,可以免受任何劳役,并且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粮食。
所以,当他们获得这个职位时,他们就必须维持生计,所以,他们的教皇派克一世曾经颁布过一条法令:“不得接受奴隶制的庇护,不得从事这个职位,也不得在神殿中享用食物。”
但是,这些命令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效果,在吉萨凯恩穆纳菲尔特的墓碑上,记录了许多关于第五王朝末年祭祀犯法的律法,说明了许多别有用心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得到了这个职位,并且利用律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古埃及的贵族和官员们,他们的法制观念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久以前,一名官员通过买卖和收受礼物获得了这片土地。除此之外,尼卡安赫、维普艾姆奈菲尔特等人也会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遗言,而有的人则会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遗言,比如第六世的威德伽·伊特吉。
他们不仅要守护他们的财富,还要为他们的死做准备。与此同时,萨卡拉地区也有一座名为“维吉尔凯格姆尼”的墓碑,以及一座名为奈菲尔塞舍姆拉的墓碑,上面都写着类似“调解民间争端,为有需求者提供司法援助”之类的字眼,这些字眼都是为了向神灵致敬,以便在来生时能够更好地向神灵致敬。
古埃及的法律对其可应用的空间的定义是模糊的。在奈菲里尔卡尔的诏书中,他把被“统治”的地区称为“诺姆”,意指“上埃及”和“下埃及”,所以,“统治”看起来是对整个埃及都有效的。而在派皮二世诏书中,他把“金字塔城”作为该诏书所保护的地区,也就是“吉萨蒙卡拉金字塔城”,所以这条诏书看来也是对当地有效的。
泰提敕令、派皮一世敕令、继承人敕令也是如此。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达,不但造成了古代埃及法的应用范围的模糊性,也使得其有了被忽略的空域。
或者,当事件发生地为一个双重负荷的法律空间,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既违反了国家法,又违反了地方法,那么,会不会被提起双重诉讼?也就是说,在发生了“地域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时,“地域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优劣,这一点,在古代埃及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古埃及的法律从来没有对那些原住民在埃及法中是否也适用,也没有对原住民在外国违法时,埃及原住民能否受到双重起诉作出任何说明。所以,在涉及到法律客体的问题上,在古代埃及的法律中,没有关于本国法究竟比他国法优越的问题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