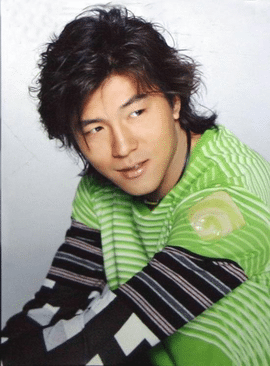在1919年的法国革命中,许多不同的阶级聚集在一个以华夫特政党为代表的、为解放而奋斗的爱国人士身边。1922年宣布独立之后,宪政民主曾经风靡一时,甚至连宗教领袖和保守派都在努力从 教义中找到支持立宪 的依据。
但是,所谓“兴隆”,是否正是由于人民对“开明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可?埃及社会各个团体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理由究竟有多深,这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前途息息相关,同时也说明了为何 的政治身份能够重新获得认可。
自由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将 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而被替代,埃及从未脱离 的政治理想,自然有着与西方的政教分离的巨大的社会根基。
自由宪政不是一种能够在任何社会中有效的单纯的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即对某种与人类本质和社会相关的理念、价值和准则的信仰。
在西欧,宪法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政治斗争,终于形成了一种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体系,它包含了人类对理性,个人自由,少数服从多数,代议制,精神和思想的自由,政治参与等价值观的信仰和坚持。
然而,埃及 的传统政治信念却是以天启式的《可兰经》和《沙里亚法》为基础,对其进行社会管理,这与西方以人类的理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理念有着本质上的矛盾。
在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还受着传统的约束的情况下,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突然冒出来的自由主义国家以及它的宪法制度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新的理念、制度和物质现实与埃及原有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模式发生了冲突和断裂,难以应对埃及 社会的紧张和压力。
现代派人士 ·阿卜杜试图克服埃及社会对西方制度的意识形态阻碍,试图将两种宗教制度融合到一起,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以阿卜杜为首的众多 学者对世俗化的国家主义持否定态度,并将其视为西方对 社会进行文化与政治控制的一种间接方式。 兄弟会的意识形态保持着这种基础观点,而哈桑·班纳则宣称, 才是 的唯一国籍,也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忠诚。
归根结底,在一般人眼中,那些倡导立国与世俗化的少数派与广大群众格格不入,他们的观点不是原创的,也不是本土的,对于底层群众最关注的民生问题置之不理,因此,他们似乎是一种别样的、毫无用处的东西。
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来维护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立宪制度。卡迈勒和鲁特菲鼓吹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确在埃及获得了以专业人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富裕阶层的长期拥护。它对自由主义国家有着强烈的反应,其原因在于它是一个脱离了常规的新的群体,对新观念的接纳能力较强。在新的岗位上,律师,法官,公务员等,均接受过大量的西方文化训练,熟悉并运用西方的专业知识和规范来思维,处理问题。
自由主义的民族立宪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与一个社会所面对的历史性难题。由于自由主义者提出立宪 是为了期望本国能像欧洲各国一样获得同样的成就。因此,按照1923年《宪法》组建的新一届新 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对埃及人民所面对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是否有效。
这就是所有埃及人所面临的真正的民族独立问题。对社会底层人民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好生活上的问题,尤其是在危急关头。但是,无论是为了实现民族的彻底自立,还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上的公正与公正,立宪政权都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使命。
在大学生活中,除就业问题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理。他们在学校里学习到了很多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所见到的只有英国的干涉,宪政的混乱,选举的操纵,党派的斗争,以及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落差,再加上自己没有工作的悲惨经历,这些年轻人难免会对国家所提倡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感到怀疑和困惑。
正是因为这种缺失,才使得人心中的 价值观的两难处境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恶化。而在此过程中,教育不但没有提供对民主政治的保障,反而造就了大批的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