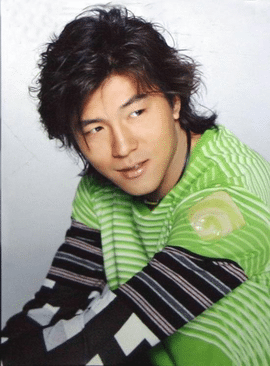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 ,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下面66历史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司马迁,生于何年,没有人知道,故乡到底在哪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有的说在夏阳(今陕西韩城南),有的说在龙门(今山西天津)。

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武帝初年担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撰录史实,秩比六百石。
不要以为太史令是个多大的官,在世人眼中,太史令近似于倡优,不仅微不足道,而且上不了台面。
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谈却格外珍视这一官职,他曾自豪地向儿子司马迁历述自上古以来司马氏一族中有多位先祖担任过史官,敦敦教诲司马迁要以“世典周史”为荣。
能够在卑微中仰视家族的荣光,这是一个有信仰并且能够将信仰传承下去的家族。
为了子承父业,司马谈很早就对司马迁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十岁前后,司马迁对《左传》、《国语》、《世本》等典籍就已经熟读于胸了。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迁徙郡国豪强到长安茂陵,司马迁也随同家族迁到了茂陵,属籍显武里。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大丈夫的一杆标尺,得益于家族的底蕴,知晓行万里路的重要,司马迁晚了两年,但也正当时候,二十岁时他只身远赴大江南北,广泛游览,神交古今。
长途一路,涉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追寻屈子旧迹,观览孔子遗风;重走楚汉争霸的风云路;受洗礼,经磨难——千里辗转回到长安后,司马迁先后又拜在了两位鸿儒门下。
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
走天下,拜名师,这一段经历对司马迁而言,至关重要,这为他植下了“史家绝唱,无韵离骚”的根基。

宏大的使命,往往是从悲剧开始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司马谈在随从汉武帝封禅泰山途中,不幸病故。临终前,老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哀泣嘱咐,一定要继承父志完成后来被称为《史记》的论著。
“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记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
听到父亲的遗言,司马迁痛哭流涕,俯首受命:“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父职,由郎中迁任太史令,开始遍读金柜石室藏书,提笔撰作大《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中年司马迁给大《史记》定下的基调,然而,就在司马迁沉浸其中之时,一场泼天大祸却突然向他袭来。
这一天,朝堂上正在声讨李陵的叛国之罪,汉武帝见司马迁沉默不语,猝然问了他一句:“卿以为如何?”
哪里知道,司马迁一开口,朝堂之上先是惊愕不已,接着便是怒目一片。
司马迁说:“(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谋蘖(nie,枝芽)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徒卒不满五千,深輮(rou,车轮外框)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兵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是真正的大丈夫呀!凭他通古博今的才智,岂能不知朝堂上的忌讳,凭他能写出历代奇谋,又岂能不知如何在朝堂上避重就轻。但当汉武帝问到他时,他没有选择虚伪,更没有像他人那样落井下石,明哲保身,而是选择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李陵仗义执言。
每读到太史公这一段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答话,黑哥都有深深的感慨,感慨太史公是真正有气节、有性情的君子。因为由衷地觉得李陵有国士之风,他见不得朝堂上的丑陋,一味地迎合上意,卑鄙地落井下石,所以他要痛斥,痛斥这一些没有人格的朝堂小人,哪怕犯了众怒,也在所不惜。
英雄惜英雄,君子赏君子!将胸中的块垒吐出来之后,司马迁为李陵做出的具体辩护之辞同样让人感慨,他没有一棒子将李陵打死,而是尽量设身处地地去看他的付出,看他的牺牲,看他的不易,诚然,李陵投降在本质上是错的、是耻辱,司马迁自己也这么认为,但在自己开口说话的这个关键时刻,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仗义。
该怎么讲这种仗义呢?
也许就是有血有肉的真性情吧。
其实,司马迁在讲完李陵之功后应该再痛斥一句李陵之罪,那样也许就不会再有后来的奇耻大辱了,怎奈热血上头时,人都是顾不了那么许多的。
汉武帝勃然大怒,是有帝王逻辑的。
在汉武帝看来,李陵不能战胜,只能战死,唯有如此才能显出他对当今圣上的绝对忠诚;不死而降,那就是对皇帝尊严的严重亵渎。

可怜司马迁,因为这一席话,结果以“诬上”大罪处以腐刑,更叫人感到凄凉的是,司马迁家贫拿不出钱财来自赎,至于亲友、同僚,不是爱莫能助,就是幸灾乐祸。
没有钱,司马迁很可怜。
不与小人为伍,司马迁很悲壮。
腐刑对司马迁这样有气节、有人格、有血性的人来说,是万难承受的奇耻大辱,但他没有愤而自杀,也没有自暴自弃。在被称为“蚕室”的幽暗监狱里,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惊人的毅力和坚韧践行了他对父亲的承诺——没有完成家族的使命,绝不能死。
信仰见于苦难,苦难使人格光芒万丈。
因为有人格,更因为有信仰,蚕室中的司马迁虽然身体残了,再无体面而言,但他并没有失去激情与棱角,相反,他像一个敢于直面苦难,永不屈服的英雄,一个在宏大史诗中持戟泣血的英雄。
正因为持笔者有这样伟大的信仰与人格,《史记》中的许多篇章才会那样的激荡人心,澎湃千年。

然而,表面沉默,内心更加激烈的司马迁终究还是没能逃过悲剧的宿命。
在蚕室中,他曾给挚友任安写过一封信,在这一千古名篇中,司马迁以刻骨的笔触表露了他内心的痛苦、人格以及信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但这又能怎样,“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遗憾的是,俗世是残酷的,也是可悲的,即便司马迁秉持的是贤圣之心,但因为坚持秉笔直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记》还是被扣上了“谤书”的帽子,武帝、昭帝时被禁,直到司马迁去世二三十年后,才因外孙杨恽的冒死进奏,得以开禁。
写完《史记》,对司马迁而言,家族的使命完成了,他的一生也就再无遗憾了。让后世唏嘘的是,一个曾为无数先贤豪杰立传的大家,却没能为自己的最终归宿在历史中留下一笔。
他到底是何时去世的?是否是善终?
后来的官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
只有东汉时期的卫宏在《汉旧仪注》中提到了一笔:“有怨言,下狱死。”
残烛燃尽,不如愤然谢世!黑哥宁愿相信司马迁死在了狱中,有史家认为就是千古名篇《报任安书》惹的祸。
······
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
英雄此日谁能荐,声价当时众所推。
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
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