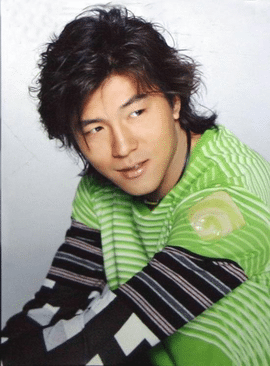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66历史网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乾隆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湖北白莲教徒正式举义反清,然而清廷年号虽由乾隆改为嘉庆,但实际上清高宗却仍然执掌朝廷大权。而“康乾盛世”之名犹言在耳,千古明君的乾隆皇帝也未龙驭宾天,可似乎随着年号更易,大清的盛世就似是如风吹雨打去。
事实上,从乾隆中、后期开始,整个清廷的统治就显现出了不稳定的态势——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四十六年、四十八年甘肃两度出现反清战事,乾隆五十一年中国台湾林爽文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倘若真是太平盛世,又岂能会出现这样规模不小,需要出动如福康安这等名将的内地叛乱呢?

要知道清朝中前期的地方安定之策,是以“州县自安,官民联防”为核心——即弹压地方民变匪乱,职责在本地绿营和团练,若平叛不顺,才需要向督抚请援,开始调动一省之力进行围剿,唯有在省级清军调动下都无法剿灭叛军,清廷中枢才会开始调兵遣将。
也就是说,大量的小规模民变匪乱其实还未上达天听,就被地方安定力量所剿灭,唯有地方不能平定的“大患”才会引动朝廷干预。
事实上,在乾隆之前的康熙、雍正二朝,能让清廷从中央调兵遣将,汇聚大兵的战事,多是如三藩之乱、西征准噶尔这个级别的战争。
乾隆中后期的接连内乱,可以说在彼时的“清朝之累”已及“难返之地”——此后的天理教之乱、太平天国之乱的祸根亦是从乾隆时期种下。
·壹····
“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乾隆四十八年,爱好写诗的清朝高宗皇帝弘历写下了这首《谷数民数》。
而这首七言绝句的背景则是乾隆中后期以来,腾贵的物价和繁衍愈多的人口。
顺治八年,清廷入关未久,当时治下户口根据统计为人丁10,633,326户,但这个账面数字不过是清廷中枢所掌握的纳税单位,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户口。
但到了乾隆年间,由于经历康熙、雍正两朝的“滋生人丁(人头税)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两项改革,对于勋贵士大夫而言,隐瞒人口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到了乾隆年间,清廷一改此前的“纳税户口”的人口清查制度,更张为了近于现代的以“人口”为基本单位的普查方法。
乾隆六年,清廷治下总人口经统计为143,411,559人,但到了乾隆四十年,清朝总人口却已经增长到了264,531,355人——当然考虑到清廷的政治管制能力,再加上乾隆以来的流民滋生,这样的人口统计数据其实仍于真实情况大有出入。

但哪怕如此,短短三十四年内就增长了超过一亿人口,这对于处在中古时代下的大清王朝无疑充满了压力。
钱泳在《履园丛华》中记载了从康熙到乾隆末年的苏南物价,康熙末年的平时米价每升七文,在康熙四十八年遭遇旱情后每升米则涨到了二十四文,而乾隆初年的平时米价虽然相较康熙末年涨幅了不少,但也不过每升十余文,可等到了乾隆五十年遭遇旱情时,每升米竟然上涨至五十文,而等到灾情过去,米价则常年在二十七文到三十四文间徘徊。
同样生活在乾隆时代的汪祖辉也提到,浙江一斗米的价格从乾隆十年时的九十余文高涨至了乾隆五十七年的二三百文之间。
而田亩的价格也随着粮价越来越高,顺治时苏南一亩田地价格不过二、三两银,至康熙时升至四、五两银,而到了乾隆末年则价高至五十两。
也就是说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的百年之间,江南的米价在平时竟然增长了两倍到四倍——而米作为封建时代民众的生活必须品,其“量大且刚”是观察当时物价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而在大米之外,其他物价也水涨船高,以至于时人惊奇的评价到“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果蔬无一不贵”。
一面是物价腾贵,一面同时也是民众大面积的贫困,在马戈尔尼使团记录的出使清廷的记录之中,有着大量的类似描述——“在普通的清朝市民里,看不见英国市民常见的大肚腩,事实上他们十分瘦弱”,而为了抢夺使团抛弃掉的鸡鸭鱼肉和茶叶,围观的清朝人会纷纷投入到水里,游去争抢。
为了求得生存,贫困的清朝人民不得不离开原籍,去其他地方寻找一线生计,但到了乾隆年间,腹内各省早已人满为患,东北和中国台湾虽然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垦殖,可由于清廷对这两地的特殊考量,一直要到同治末年甚至日俄战争之后,才开放这些地区的垦殖禁令。
(晚清民众)
事实上,川楚教乱的根源,就是因为百万无业可为的流民聚集在了川楚之交的地带上进行“无照垦殖”——清初顺治时虽然就开始实行“垦政”,可地方官府在“招巧流民”之后,流民需要获得“垦照”才能进行荒地的开垦并享受一系列的“垦荒福利”,但事实上出于管制考量和笼络士绅,一般升斗小民很难获得“垦照”,唯有富豪士绅之流才能享受这一样政策。
一面是物价飞涨,一面是活路难找,可清朝民众的苦难远远不止于此,乾隆中衰也不只是清朝社会的自然演变。
··贰···
清代巡抚的合法年收入是一百五十五两,两江总督的合法收入为一百八十两,而在雍正元年时,清世宗要求各地督抚上报收受“陋规”的情况。山东巡抚表示,其人陋规年入为十一万余两,广东巡抚则称自己每年收入为六万余两,河南巡抚则表示一年陋规为二十万余两,两江总督亦称一年陋规收入为近二十万两。
也就是说,哪怕陋规收入最少的广东巡抚,其灰色收入也是合法收入的数百倍之多,而如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则越千倍不止。
雍正阅览之后,对时任广东巡抚的年羹尧御笔亲批写下“览尔所奏,朕心甚悦。全是真语,一无粉饰...”之语——作为夺嫡的胜出者,雍正曾经办皇差多年,不管是京中规矩还是外地细务都有所了解。
而他之所以在登基之初,就下御旨了解各地督抚的陋规情况,其政治目的却是与其人素来“苛细”的评价无关——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以来贪污之风盛行,原因就是因为官员合法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实际上的开支。
希冀官员“枵腹从事”,既不现实也无益于政治。
所以一场对“陋规火耗”的合法性改革,旨在提高官员收入又不实际增加百姓负担的“养廉银”和“火耗归公”改革便在雍正初年提上了日程。
“陋规”和“火耗”其实是清代的“亚财政”,因为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演进,核心思路就是“强干弱枝”,中央在财税制度的演变上,其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大,地方所分则越来越少。
清初承明制,财税提留比率为7:3,但到了康熙年间,清朝认为前明覆灭的原因是因为“失之以宽”,因此将财税的提留比例进一步的提高到了82:18。
这就导致地方不仅需要自筹费用兴办教育、修建道路等,甚至就连地方衙门的正常开支,都需要自筹。
以地方督抚为例,巡抚“察院”和总督衙门作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机关,需要有大量的幕僚和其他公务人员作为经办人,可实际除了巡抚和总督本人以外,其衙门成员并无官方编制身份,而这些人员的开支则一并都需要督抚承担。
同时,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官场之上的社交关系更是复杂,例如科考系统下的“同年”、“房师”、“座师”,地方上的“同乡”等,往来接济都需要官员提供不菲的开支。
一位巡抚或总督,想要解决正常的个人社交和衙门开支费用,根据学者统计,往往需要八千到两万余两白银不等,而这笔费用是督抚官员正常年薪的数十倍到百倍不止。
这样的财务需求,也导致自明以来的陋规和火耗一直都被政治体系所知晓且包容。
所谓“陋规”,其实是下级衙门向上级衙门和乡绅对官员,以规、礼、费、敬之名的“上供”,以江西巡抚衙门的规礼为例,一是节礼,乡绅和官员,在进行参谒、适逢节日时,向巡抚进行馈赠。二是漕规,由漕务方面所送。三是关规,江西境内的税关衙门向巡抚衙门所送。四是盐规,由盐商馈赠,最后则是钱粮平头银,由布政使司孝敬。
火耗则是更具有普遍性的“灰色收入”,从狭义上来讲,这是地方衙门对运输途中的“漂没”成本和“银两重铸”时产生消耗所加征的“额外钱粮”。但在清代的实际操作中,则成为了地方衙门征收“附加费”的表面名目——可相对于苛捐杂税,火耗对于地方百姓而言,其实反倒显得很“正额”。
而这些费用在雍正进行火耗归公后进行了合法化,将之重新划入到了监察体系之中——正如前文所述,督抚正常的需求费用不过八千到两万两左右,可实际上的陋规收入有近八成甚至更多的落入到了官员个人手中。
在雍正改革过后,清廷通过“火耗归公”,拥有了更多收入,并通过“养廉银”给予官员进行变相提薪——在“养廉银”制度实施后,总督每年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则为一万两左右,相较此前合法收入,增长了近百倍甚至更多,而州县官员的收入亦提高了数十倍。
养廉银的实施使得清代在雍正时候的吏治大幅好转,并且由于多余的“陋规火耗”不再进入官员个人腰包,地方财政得以宽裕,各地赈灾能力也大幅提升,间接使得彼时的清代治安亦获得了恢复——在康熙晚期,就连北京都出现了“辇毂之下聚数十万游手游食之徒,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所”,以致于在“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都爆发了陈显五、朱一贵等起义。
但等到乾隆继位后,这位矢志要为大清奠定“千古不易之制”的皇帝,对养廉银的改革,彻底葬送了雍正皇帝的政治遗产。

在雍正皇帝的设定下,养廉银制度是一个根据地方官员汇报当年相关财务数据后的动态制度,随物价、灾荒等事件进行波动,可乾隆皇帝继位后为便利后代,防止后来的皇帝被地方官员所蒙蔽,就将养廉银从“动态制度”上转变为了千古不易的“固态制度”。
然而从乾隆初年到乾隆末年,清朝经历一轮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米价都上涨了数倍之多,更何论官员迎逢所需要的奢侈品?根据学者估计,从乾隆到嘉庆年间,清廷的物价平均增长了差不多三倍,官员开支压力增加,但合法收入却丝毫不变,贪腐的硬需求再次出现,也无怪乎养廉银在乾隆之后难养廉了。
而官员在“火耗归公”之后再征“火耗”,民众负担因为贪腐需求而加重,再加上物价昂贵,民众求活无门,致使地方治安压力陡增,朝廷在镇压叛乱上的开支亦节节高升,为了弥补这些开支缺口,清廷又不得不对养廉银进行折扣发放,以弥补军需——以致于官员们感叹腐败贿赂公行于世,但真正出于贪渎的少,为现实所迫的实多。
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