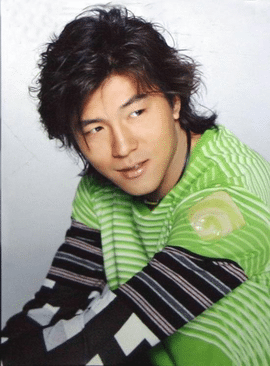彝族舞蹈,哑神舞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色。哑神舞

无量山云消雾散之后,你会看到一个青砖红瓦的小村庄,爬在无量山的半山腰。村庄坐南朝北,放眼可看到高峡出平湖的澜沧江,山脚是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梯田。时值深冬,在油菜花的映衬下,梯田充满油画般的梦幻色彩。柿子红得耀眼,袅袅升起的炊烟,添了一笔人间烟火的生动。
这就是南涧彝族自治县公郎乡盖瓦洒村。一场哑神舞让这个小小的村庄远近闻名。无数次奢想一睹哑神舞,那份能把无量山的神秘演绎得十分精准的民间艺术,那场踏起尘灰可以遮月的舞蹈。可是神秘的哑神舞一年只有一次演出的机会。
随着金庸先生的大笔,无量山一夜之间家喻户晓,然而深入我内心的却是一出戏。没有无量剑冷冷的光影,没有清溪涧水之上的凌波微步,只有一组简单的动作,让这出叫哑神舞的舞蹈,留在心中。
鼓点就是最好的语话,仿佛由远及近的滚雷,像是呼唤,又像是呐喊。戴着面具的舞者不知从哪里蹿到舞台中央。舞者诡异的动作,除了粗犷,还有似磐石的坚毅与樱花的柔情。幽默的元素,始终在每个动作里穿插。让观者捧腹大笑的戏,不过是民间一些细碎的琐事,或爱或恨。你永远也不会清楚何人在舞,他或许就是邻居,或许昨天还与你一块下地干活。哑神舞表演十分简单,舞者身着短裤,头戴神秘的面具,你只能凭借那一组组动作,遥想一个民族的从前。舞者不能出声,哑神舞因此得名。
任何民间的舞蹈,都有其深厚的根,哑神舞也不例外。
相传两百多年前,无量山下有一座名叫阿须落的村庄,因为世代生哑巴,乡亲请一道士来看,道士微闭双眼,信口说此地有哑巴神作怪,需用法术驱逐,于是乡亲就跳起“哑神舞”。又说,“哑巴神”到与阿须落村相邻的盖瓦洒作孽,所以每年二月初八,盖瓦洒村都要跳“哑神舞”。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今,尽管今日当地的孩子聪明好学,姑娘美若天仙,再也没出现过什么哑巴,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它在舞蹈中延续下来。
我观看的哑神舞,是今年冬天临时安排的一场演出。尽管是临时安排的演出,但对于尊神的彝族同胞,他们丝毫不敢怠慢,也许他们曾经许诺过,每年只演一次,但现在需要演出,只有重新敬神。104户彝族同胞,每户出一人方式参与敬神,在村后的山神庙内杀鸡宰羊,敬献山神,选举出“哑神舞”的六名“会头”。会头的主要任务就是主持“哑神舞”的全部事宜,并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通过占卦选出“哑神舞”的8名舞者。
不是节日,却引来了当地许多人参与其中,村民们纷纷穿上节日盛装,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夜幕降临,男女老少齐集村中广场,点燃篝火,随着芦笙欢快的旋律,围着熊熊篝火“打歌”。
哑神舞的8个男舞者,其中3人扮男哑巴,3人扮女哑巴,2人扮孔雀,而哑巴又配成3对夫妻。男大哑巴手持木棍,男小哑巴手持木刀。女大哑巴手持木剑,女小哑巴手执扫帚,二孔雀身披绿色棉毯,头带木瓢,瓢把朝前当孔雀嘴,身后拖一竹蔑尾巴,上缚荨麻。六人的胯下各挂一铁铃铛。当村中的舞场正处在高潮的时候,“哑巴”们在会头的带领下突然冲入舞场,顿时鞭炮齐鸣,鼓声震天。狂歌劲舞的男哑巴可以对舞场上的少女嬉戏,看上谁拉谁,被拉的少女也不能生气。30分钟后,打歌的人们自行离去,在家等候“哑巴”们的到来。
“哑巴”们在会头的带领下,挨家挨户起舞。首先由扮演丈夫的男哑巴进入主人家的正堂内狂跳一圈,接着其余哑巴加入狂舞,舞者没有固定格式和规范动作,完全是随心所欲的发挥。他们可在床、桌、房、墙各处使劲乱跳,纵然踩到桌子、椅子、床板也在所不惜,若把床板跳断,主人反觉吉祥。舞蹈时,“哑巴”们手中器物可乱砍乱戳,小女哑巴手持扫帚沾水,不时洒在主人和观众身上,男小哑巴不时将水喷在拥挤的人们身上,以示令其让道,两只孔雀左右开弓,时而用嘴啄人,时而用尾巴撩人,其真正的原因是怕观者离他们太近,看清真面目。20分钟后结束一家,离开时主人要给会头送上三炷香、一碗肉。众舞者出门时主人道谢平安,并大声吼叫驱逐之声,以示将妖魔鬼怪驱出家门。
哑神舞不过是盖瓦洒彝族先祖们面对神秘的大自然,逐渐产生的一种驱灾去邪、娱人娱神的民俗,在今天看来,又演变为一场盖瓦洒村民们的狂欢。劳动之余,人们享受舞蹈带给人的愉悦,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了生活的品位。
哑神舞最神秘的莫过于演员,那些看上去同样的脸谱后面,也许是一张缀着岁月风霜的脸,也许这个人像我一样苍老。当他们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或趴在大地,跪求珍贵的雨滴,或面向佛祖,祈祷命运的恩赐,留给我的除了感动,还能有什么?
谁也不知道舞者从何处来,他是孩子的父亲,还是父亲的孩子?哑神舞靠粗线条的勾勒,甚或是手打不直、脚抬不稳的动作,在无法明晰的情节里,如品无量山茶,解渴之后才能回甘淡淡禅意,说不上优雅,却是一个彝人村庄百年时光里的淡淡哀愁与忧伤。
一位演员的面具被风吹落,在他急于追回被风卷走的面具时,我看到他瘦骨嶙峋的双手。我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他紧紧裹着的毛草,与唯恐落地的面具,就是他创造微薄收益的工具。以至在离开无量山的许多日子里,我仍然为哑神舞难眠。
哑神舞也在被人包装着,走到了五彩缤纷的灯光下,经过专业编舞校正的动作失去了粗犷,在种种规定和格式化的动作中,也就失去了哑神舞作为原生态舞蹈的价值。有人来到盖瓦洒,试图用金钱请哑神舞进入象牙塔,与其说是让这出源于无量山间的乡土舞剧安放上现代元素,不如说是往本来很民间的精神食粮上贴上市侩和浮躁的标签,从某种意义上砍伐掉哑神舞该有的尊严。
就在演出结束演员们卸妆时,我看见一位舞者嶙峋的骨骼,好象就在胸部,刹那间联想到无量山,供许多人寄存想象之剑的千仞悬崖。